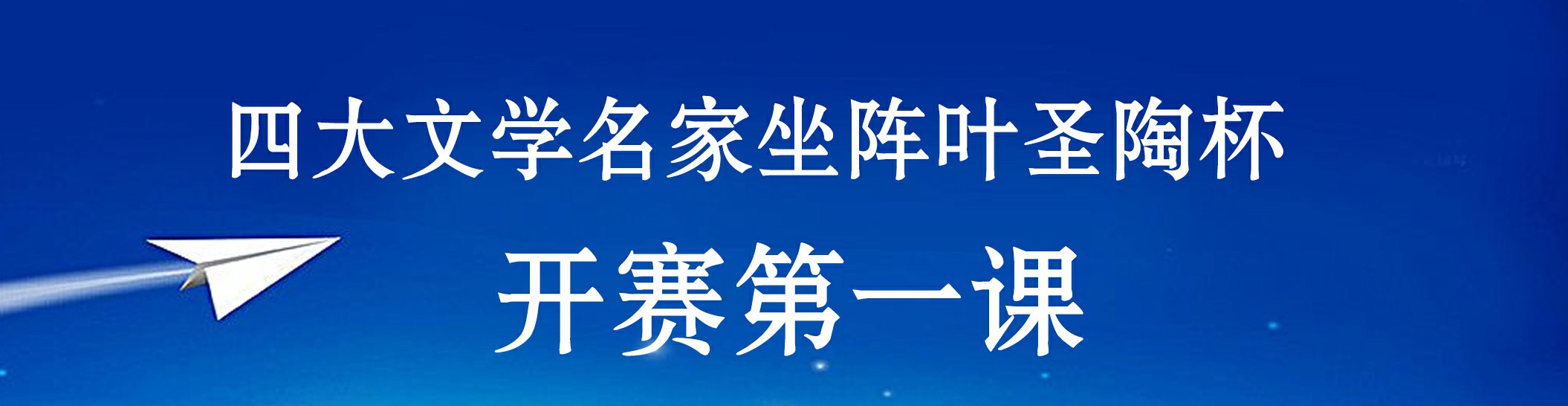曹文轩:有汪曾祺这样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运气
2022-06-07来源:读书公会
编者按:曹文轩不仅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中国大陆首次开创“创意写作班”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通过常年对文学的写作、教学、思索,他将自己对文学技艺的提炼和对文学精神的感悟,融入到对经典作品的鉴赏之中,写出了《经典作家十五讲》。书中解读包括鲁迅、沈从文、钱锺书、契诃夫、川端康成、普鲁斯特、毛姆、卡尔维诺等14位作家及作品。最近网络对曹文轩作品颇有争议,特转发其《经典作家十五讲》中谈汪曾祺作品一文供读者辨别。
水洗的文字——读汪曾祺
文|曹文轩
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在西南联大读过书,1949年以前就写过《复仇》、《鸡鸭名家》等很别致的小说。1949年以后主要精力投放在戏剧创作上,是京剧《芦荡火种》的执笔人。这个剧后来成为样板戏之一的《沙家浜》。
他重新写小说,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品发表后,有见识的读者和评论者,都有一种惊奇,觉得总在作深沉、痛苦状的文坛忽地有了一股清新而柔和的风气。但却因他的作品一般都远离现实生活,又无重大、敏感的主题,并未立即产生大的轰动,倒显得有点过于平静。他是越到后来越引起注意的。当那些名噪一时的作家和红极一时的作品失去初时的魅力与轰动效应而渐归沉寂时,他与他的作品反而凸现出来。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汪式“风俗画”
当许多年轻作家拜倒在现代观念的脚下、想方设法寻找现代人的感觉、竭力在作品中制造现代氛围时,汪曾祺的作品却倒行逆施,追忆着过去,追忆着传统,追忆着原初,给人们酿出的是一股温馨的古风。
古风之生成,与风俗画有关。他对风俗画的追求是刻意的。
追溯到现代文学史,在小说中对风俗画的描绘始于鲁迅先生(如《祝福》、《社戏》、《孔乙己》等),沈从文的《边城》则是风俗画的一个高峰。这条线索,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断了。因为,这种美学情趣,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又由汪曾祺将这条线索联结了起来。
这里不去引用《受戒》的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整篇《受戒》都是风俗画。我们从他的《异秉》引用一段:
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到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清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猪头肉则分门别类的卖,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用名词,叫“大肥”。要什么,切什么。到了点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吃完晚饭,总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生意,他不忙收摊子,他端了一杯热茶,坐到保全堂店堂里的椅子上,听人聊天,一面拿眼睛瞟着他的摊子,见有人走来,就起身切一盘,包两包。
从《大淖记事》里再引一段:
他们也有年,也有节。逢年过节,除了换一件干净衣裳,吃得好一些,应是聚在一起赌钱。赌具,也是钱。打钱,滚钱。打钱:各人拿出一二十铜元,造成很高的一摞。参与者远远地用一个钱向这摞铜钱砸去,砸倒多少取多少。滚钱又叫“滚五七寸”。在一片空场上,各人放一摞钱;一块整砖支起一个斜坡,用一个铜元由砖面落下,向钱注密处滚去,钱停住后,用事前备好的两根草棍量一量,如距钱注五寸,滚钱者即可吃掉这一注;距离七寸,反赔出与此注相同之数。这种古老的博法使挑夫们得到极大的快乐。旁观的闲人也不时大声喝彩,为他们助兴。
婚丧礼仪、居所陈设、饮食服饰等等民俗现象,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当然,又绝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文学毕竟不是民俗学。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土风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出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发展,或是用于整个作品情调的渲染,都有一定的用场。
如此喜好,也许与他的老师沈从文有关。沈的作品,风俗画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即为川东交易接头处,因此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的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缆与灌锅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的长案上,常有焦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里插着大把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出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家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来到身边的案桌上了。(《边城》)
这些淳朴的风俗画构成了沈与汪的文学世界。
在他二人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上的人”,或“这个小城”。《受戒》开头,只说了两句就说到了“这个地方”。说了“这个地方”之后,必然是一段有关“这个地方”上的风土人情的描述。
文学史上,倾倒于风俗画的大作家不乏其人。因为风俗是与社会发展,与民族性格和精神密切相连的。从风俗的变化,可以发现社会发展和民族心理变化的轨迹。一部《红楼梦》,便是一部“中国风俗大全”。老舍曾在对吴组缃先生的长篇小说《山洪》作出较高评价之后,指出它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对有关民间风俗描写不够。吴先生以为老舍先生所言极是。
汪曾祺要让人们看到他的“清明上河图”,看到种种特殊品格的文化。
迷人的道德气氛
汪曾祺笔下的社会,是一个基本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比较原始。这个社会追求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理想,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分工简单,家庭是共同劳动的经济单位。大部分是以土地为其经济、生活、文化、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他们的生活都围绕着村落。
近些年我们有一批作家,对这种古老的渔猎、放牧和村社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从令人目眩的现代社会走出,或溯时间长河而上,寻找昨天的部落和村落,或走进大山、原野去寻找一片至今还未经文明社会熏染的土地。
汪曾祺所写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苏高邮地区的小镇和村社生活。三四十年代,从整体而言,中国当然已开始向现代文明社会迈进。但就这个特殊地区来说,却还在较为原始的状态之下。它远离文明的大都市,发达的水路交通除了给它带来热闹,并未带来现代社会的新观念。它在变革,但仍保持着原始的特色。“田畴麦垄,牛棚水车,人家墙上贴着黄色的牛屎粑粑——牛粪和水,拍成饼状,直径半尺,整齐地贴在墙上晾干,作燃料⋯⋯”(《大淖记事》)汪曾祺很乐于描绘古老的村社图景。小街小巷、鲜货行、作小本经营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小商贩、各行各业的小手工作坊、笨重的生产工具、简单粗糙的铸造⋯⋯虽然也有“漆得花花绿绿的”、“机器突突地响,烟筒冒着黑烟”的小轮船(蒸汽机的发明当然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的标志),但用今天的目光来看,它的整个生活画面毕竟还是涂满了原始的色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有大量的描写土地为中心的乡村山野生活、把古老的农业社会浪漫化了的作品——“农村是上帝创造的,城市是人创造的。”
主宰这里的生活的是一种与今天的道德观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始道德观—— 一种童话式的道德观。
汪曾祺的作品洋溢着这样的道德观的迷人气氛。他的小说也自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未达到振聋发聩、令人心情激荡的程度,但却会使人在心灵深处持久地颤动。这种力量正是来自于这样的道德。《大淖记事》是写一个小锡匠与一个贫家女子的爱情故事。这种爱情闪烁着未经世俗社会熏染的人的原始品质的光辉。当巧云还未来得及将自己全部奉献给小锡匠时,却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粗暴地占有了。巧云为小锡匠未获得首夜权而感到深深的惋惜与内疚。她有一种自发的道德破损感。面对自己所恋的人被玷污,小锡匠并未产生现代人那种厌恶、嫉妒、恼怒和种种不可名状的心理,却时常夜间偷入巧云的茅屋,去用感情的胶汁弥合一颗破碎的心灵。这与其说是对肉体的占有,不如说是一种勇敢的、纯洁的道德行为。而这种道德以及施行这种道德的方式都显然不是现代人的。作品越往后写,这种传统道德观所蕴含着的善的力量则越强大。小锡匠被刘号长派人打了,巧云让锡匠们把他抬到自己的家中。锡匠们凑了钱,买了人参,熬了参汤。“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小锡匠。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了出来。”后来,这些锡匠们组成了一支游行队伍,上街示威游行。“他们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个带中世纪行帮色彩的游行队伍十分动人。”这种力量强大得使地方当局都感到惧怕,不得不将刘号长驱逐出境。他的《岁寒三友》中的清贫画师靳彝甫,与朋友相处,竟只“义气”二字。当他的两位挚友破产、家徒四壁而感到绝望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在任何困难时刻也不肯出手的祖传珍宝——三块田黄石——出卖了,慷慨地去营救正走向死亡之路的朋友。他的《皮凤三楦房子》中的皮凤三很有点明清话本中的人物的色彩。他仗义疏财,抱打不平。对于倚财仗势欺人的恶者,他常常“用一些促狭的方法整得人狼狈不堪哭笑不得”。
所谓道德,是社会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们依据一系列道德概念生活,与周围的人相处。中国传统道德的内容不外乎是:善、侠义、豪举、慷慨、为朋友不惜囊空如洗两肋插刀、诚实、专注、绝不背信弃义、怜贫、怜弱、扶危济困、一方有难八方相助等。中国人沿用这种道德观,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道德观相比,它可能是落后的。它远没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也没有受到政治观念的影响,更无阶级意识。它是原始的,但又正因为它原始而格外显得纯真、不带虚伪、富有感动人的力量。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简单否定昨天的道德观。评判它时,需有时间和空间观念。而且应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同一时间里,在不同空间(特殊环境中),旧的道德观仍然是人类优秀品质和良知的体现。在那里,它就是合理的,也是值得赞美的,尽管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来讲,它终究会成为明日黄花。
感情像纽带一样联结了人们,维系着他们的生活。但感情方式是原始的。它坦诚、直露、强烈、单纯、富有野性,与婉转、曲转、缠绵和温文尔雅的现代感情方式形成明显对比。这是汪曾祺笔下的小锡匠在被尿碱灌醒后与姑娘的一段对话:
同样,在《受戒》中也有这样的情景。当明子受戒之后,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从此以佛规来约束自己的形象——他受戒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却是与小英子悄悄划船进入了芦花荡。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与城市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相比,乡土社会,特别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乡土社会,人的关系显得格外密切。由于物质的贫乏,家庭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经济单位。生存的愿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东家缺东西,便去西家借,大至大型劳动工具(如水车、牛马),小到一升米、一根针。他们需要互相扶持,互相依赖,谁也离不开谁。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他们之间只能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有很多作品在写这种社会里的农民阶级那种自然纯朴的感情,使有感于都市化带来的感情淡化的广大读者与这种旧式的、历史将要结束它的感情发生共鸣。
“遥远”之美
汪表现原始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出于美学方面的考虑。
“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美的事物往往有一点‘遥远’,这是它的特点之一。”对于现实世界,一般的人们所注意的往往是它的实用价值,而不太容易对它采取审美态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个现实世界,人们再回首看它时,由于它与他们的生活已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往往就不带经济中人的世俗眼光了,而站在了一个审美角度上:不是这件物体值多少钱,有什么实际作用,而是这件东西美不美。一口古钟,也许已不再是用来召集村民的一种信号,它给人们的是精神方面的感受。山顶,一座过去用来抵御侵敌的古堡,也许早已失去了它的物质性的作用,但它却能使后来的人在心里唤起庄严的审美情感。“济慈著名的《颂诗》中不朽的希腊古瓶,对于西奥利特的同时代人说来,不过是盛酒、油或这一类家常用的器皿而已。‘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
古朴本身就是一种美。
汪曾祺作品所产生的美,正是这样一种美。
洞穿一切的沉静语言
人们对汪曾祺的叙事态度印象很深。“叙事态度”是一个比“语言风格”更深刻一层的概念。对“语言风格”的分析,到语言本身为止,它并无通过语言表象看到背后的作者的人生态度的任务。汪曾祺的叙事态度是在与绝大部分中国小说家相比之下被人注意的。大部分中国小说家,所显示的是一种全身心介入生活的态度。在充满主观和感情色彩的语言背后,是一些热情洋溢的、豪情奔放的、悲愤的、焦灼不宁的心灵。他们富丽堂皇地装饰着句子,让句子积压着沉重的情感。而汪曾祺所塑造的是一个老者的形象。这位老者饱经风霜,岁月已经将他性格中的焦躁、热情、仇恨等已经干净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已去净了“火气”。现如今剩下的,是一片参透世界、达观而又淡泊的心境。他不再把悲哀、欢乐等感情看得多么严重,不再不加掩饰地将这些情感直接流注于笔端。他是一个旁观者,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了然在心,并且承认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长吁短叹。他用古朴、平淡、自然的句子,不在意地叙述着人和故事,其中含着洞穿一切的冷峻和谐趣。
这是《大淖记事》中的一段文字: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断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
汪曾祺心平气和地面对人生,面对自然,悠闲地驾驭着文字,简洁、明了地叙述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来看另一位作家的一段文字。这里我们并无褒贬之意,而只是想通过这段另一极端的文字,与汪的叙事态度做一个比较,从而更清楚地看出汪的叙事态度的不同:
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叩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低哑呻吟的拍节上,新的一句在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尽心尽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
这段文字为张承志所有。他是以一个深沉的、充满激情的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的,与汪的淡然相反,是一个完全投入的姿态。
叙事态度背后,总有很深的文化以及人生的背影。这绝不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是文化品质长期渗透和人生经验的积淀。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语言风格千差万别,也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习惯问题。对叙事态度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定会超出以往研究“语言风格”时所获得的浅显见解。
叙事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语气(或叫口气)。分析语气是研究言语人之身份、品质与趣味的一个重要途径。语气的微妙区别却可能隐藏着叙述者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气质、不同情趣和不同的教养这样一些重要事实。其实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第一句,就可能透露了这一切差异:
1.我的妻子
2.我的妻
3.我那口子
4.俺老婆
“我的妻”仅比“我的妻子”少了一个“子”字,但给人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我的妻”,这种口气是一个文化人的口气,并且是一个性格平和、感情纯正并略带了一些酸腐的文化人的口气。
汪曾祺的叙事态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他的生活经历。汪1920年生,写《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时,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这漫长的人生历程,使他对社会,对生活,都有了很深刻的感受。他的人生道路又极不平坦。如此人生,使他获得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平淡品质。他已将人生识破,忧愁和苦难,在他来说,都已不再可能使他产生大弧度的感情波动。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名士的汪曾祺,已进入了一种境界,一种徐渭式的境界。徐渭有两句话,叫:
乐难顿段,得乐时零碎乐些
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
汪曾祺既不会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也不会像张承志那样因为幸福而泪水盈眶、伏倒于草地而亲吻不已。
说到汪曾祺的叙事,不能不看到第二个原因,即他的旧学根底与古文的熏陶。汪的语言,凝练老成。他不少散文,其实是用半白话半文言写成的。古汉语有这种气质。与此相比,现代汉语有浮华轻飘的一面。他从古汉语那里得到的是一种语言的沉静。他得了古汉语的一些精神。
语言最小的意义,大概可见一个人的气质,而最大的意义则可见一个民族的气质。古代汉语曾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气质形成中起到过看不见但却极深刻的作用。但“五四”时期必要的却又极端化了的反文言,加上后来对文白之争的误读与偏读,使我们与古代汉语决断,一味亲近白话,从而使我们丢失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这是历史的遗憾。然而因多年的误读与偏读,已积重难返,这种历史的遗憾可能要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我曾劝过学写作的同学,去打一打古文底子,甚至具体地让他们看一些文章。其中,我提到一个人——林琴南(林纾)。此人不懂英语,但翻译过一百多种外文书,是用文言翻译的,极有味道,看个十本二十本,笔下再出文字,那文字的质量就很不一样。语言也有质地,像人的衣服。常习古文,语言质地就会好一些。
汪曾祺证明了这一点。他虽然不再用文言写作,但古汉语的神气却在字里行间。
说到汪曾祺的叙事态度,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在他的人格组成中有着道家精神。这一点,也早被许多研究者指出。汪本人也是默认的。这是极重要的一点。道家讲淡泊,讲宁静,讲无为。这种人生态度溶化在血液之中,自然而然地要反映在他的叙事态度上。
有汪曾祺这样一个作家,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运气。他的价值似乎超过了他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他的出现,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趋向的调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改变。
但从他本人作品的文本价值而言,我们说:汪曾祺是名家而非大家。
无论从他作品的数量上还是从他作品的分量上考察,这个结论都是符合事实的。
确实,他不是走的一个文学大家的路子。
这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深刻性以及艺术的创造性诸方面,都能看出这一点。
这些作品的背后少有宏大的哲学背景,少有那些大家所具有的形而上的题旨。
从现代形态的文学来看,文学已经走过了那个模仿现实的历史。它正与哲学融合,走向形而上——即对更本质的现实进行抽象,已成潮流。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质量还不够理想的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哲学根底。
对此,汪曾祺本人似乎很不以为然。他几次有过这样的意思:只要将生活很切实地写出,诸如哲学一类的思想自然也就包含其中了。
我们反过来问一下:没有足够的理论(哲学)力量,现实能够被你把握吗?
没有理论的观察,其实是不存在的。
观察的质量取决于主体的理论准备。空洞的观察永远还是空洞。理论是观察的驱动力。它给了观察以主题和目标、一种穿透事物而抵达最后的本领。
来源:读书公会
- 上一篇:叶小沫:我的爷爷叶圣陶,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
- 下一篇:美文欣赏|高洪波:绿友
-
复旦附中名师追寻语文教学之道..
2024-04-01
我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其实是因为一连串的意外,在我小的时候,是万万想不到自己将来会从事这个行当的。.. 查看详情 -
郭娟:卞之琳的诗文与青春往事..
2024-01-12
卞之琳的诗,是让人着迷的一个谜。诗都不长,字句端丽明白,意涵幽远,似乎感受到什么,却又迷蒙着,不可清晰道出。如眼.. 查看详情 -
铁凝 : 锤炼语言,不能光说不练..
2023-12-15
当我们具备了感受生活的能力,也有意识地去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对理解生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 查看详情 -
蒙曼:诗歌赋予人们感知美的能力..
2022-12-23
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类节目打破“次元壁”,圈粉不少年轻人 。在网上,也有不少人乐.. 查看详情
-
教育部公布2022—2025学年 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活动通知
-
第十八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启事
-
教育部公布2020-2021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2020—2021学年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的通知
-
赏读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立君的散文
-
17年17届“叶圣陶杯”新作文大赛获奖精选图书出版发行
-
喜报来啦!十七届叶圣陶杯十佳小作家张天娇被世界顶尖大学录取
-
中国校园文学馆征集资料启事
-
《第十七届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问世
-
《中学生》杂志“新作文高中月刊”征稿启事
-
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颁奖典礼在泰州溱湖成功举办
-
第十七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现场决赛山东赛点成功举办
-
第十七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现场决赛河北赛点成功举办
-
第十七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现场决赛湖南赛点成功举办
-
第十七届“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现场决赛江苏赛点成功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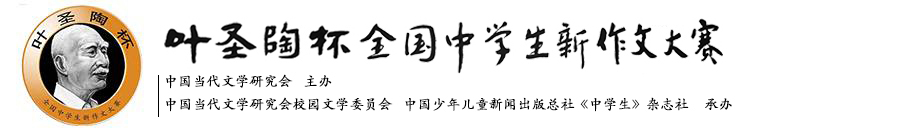
 叶圣陶杯大赛
叶圣陶杯大赛
 叶圣陶杯官微
叶圣陶杯官微
 校园文学研究
校园文学研究